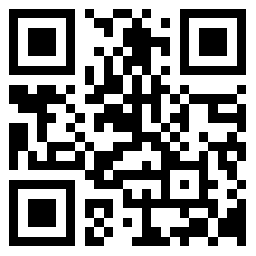艺术论坛
《酸寒尉像》 任伯年
晚清时局中上海滩崛起于东海之滨,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块高地。一时风云际会,江、浙、皖、鲁、川等地的人才和资源如滔滔江水汇向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十里洋场。这便是可以和清廷首善之都“京派文化”抗衡的“海派文化”诞生背景,能形成晚清中国文化格局中京海争锋当是一个观念自由、文艺繁荣的奇特社会现象。“海上画派”是“海派”构成一个重要方面。任伯年和吴昌硕被中国绘画史称为“海上画派”前后期代表人物。一幅画的作者和画主兼备双雄,乃之所以选择《酸寒尉像》作为本书收官之作原因之一。
生于1840年的任伯年比吴昌硕年长4岁。吴昌硕先任伯年迁居苏州,光绪八年(1882)并由友人荐作“作贰小吏”。他们的初次见面当是他们客居苏州的这段日子。有资料称1883年春天吴昌硕慕名趋府拜望海派书画翘楚任伯年,吴欲拜任为师。有资料称任见吴金石书法功力了得,颇激赏。这便是后世所谓“互为师友”一说的由来。作为二人知交见证,任伯年为吴昌硕画过多幅肖像,传世的先后有《芜菁亭长小像》《棕荫纳凉图》《酸寒尉像》等。《酸寒尉像》图虽是后作,草草逸笔,唯图一人,不似另外两幅皆有景物烘托、内容丰富,然能以后胜先,以少胜多唯“传神”二字可以解释《酸寒尉像》图的魅力。吴昌硕当时“作贰小吏”种种心态毕肖于现,加上画家以官服马褂图其貌样,应该画的是初次见面时的情状。作为职业画家任伯年默记默写功夫,不因时光流逝而淡忘,却由惊鸿一瞥而精彩。技近乎道的中国画独特造型语言,直可与西画比肩的绝佳案例。
当代坊间对任、吴关系有颠倒之说,不少人认为吴缶老成就在任伯年之上。一些公允之说也是称二人难分轩轾。难分未必不能分。众说纷纭的原因,摒弃艺术本身,主要还是后生几年的吴昌硕比任伯年多活了几十年,又有王一亭、齐白石等学生有意无意间为其抬轿子,声誉日隆也就不奇怪了。中国文化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我们更不必纠结应该给任吴二人区分金银。任、吴二人高山流水之谊是一段“海上画派”佳话。任伯年去世时,吴昌硕撰祭联:“画笔千秋名,汉石隋泥同不朽;临风百回哭,水痕墨气失知音。”当事人为两人关系早已作了盖棺定论。
回到《酸寒尉像》图本身,浙江乡贤杨岘老人的长题也不可不补记一笔:“何人画此酸寒尉,冠盖丛中愁不类。苍茫独立意何营,似欲吟诗艰一字。……”至此《酸寒尉像》解读差可告一段落,以下皆可谓题外话。
本书再版有炒冷饭之嫌,只是在十几年前出版的原书基础上加了新序和几篇延伸阅读。唯一增加的内容就是任伯年这张《酸寒尉像》。中国画人物画对“传神”的强调带有很浓的中国式品味和特质。即并不特别强调精细地观察与解剖客观对象,而是把观察感受的表现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同时又举重若轻地似乎是不经意间完成这一切。这和强调数学般准确与理性精神的西方由希腊艺术至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脉相承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区别。
任伯年生活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是新时代到来前的风雷激荡,也是旧山河破碎中的风雨飘摇。而作为创造经典艺术家,无论他表现是什么,一定会留下时代的刻痕。人物画在这一方面更有其直观敏感同时又深刻凝重的特殊性。创作中的艺术家和表现对象之间一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后世的解读又使之超越时空进入多维存在。中国画消亡是必然的,中国画精神是永恒的 。《酸寒尉像》图化古为今,虽是为一人造像,涵盖的却是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缩影。统观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遗存无不例外皆有此两大特质。
今天看来,中国画经典构成的两大要素即历史感和时代性。历史感可以用有古意来指称,而时代性则是艺术家的作品能否发时代之音。为时代立言可以是高居庙堂的黄钟大吕,也不排斥坊间草间之不绝虫鸣。余将中国画思想归纳为新六法:形为体,诗为魂,笔为主,墨为臣,色为花,气为命。如此观照《酸寒尉像》图。
刘传铭/文
《酸寒尉像》是光绪戊子年(1888)任颐(伯年)为吴俊卿(昌硕)绘制的人物画。
![]()
晚清时局中上海滩崛起于东海之滨,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块高地。一时风云际会,江、浙、皖、鲁、川等地的人才和资源如滔滔江水汇向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十里洋场。这便是可以和清廷首善之都“京派文化”抗衡的“海派文化”诞生背景,能形成晚清中国文化格局中京海争锋当是一个观念自由、文艺繁荣的奇特社会现象。“海上画派”是“海派”构成一个重要方面。任伯年和吴昌硕被中国绘画史称为“海上画派”前后期代表人物。一幅画的作者和画主兼备双雄,乃之所以选择《酸寒尉像》作为本书收官之作原因之一。
生于1840年的任伯年比吴昌硕年长4岁。吴昌硕先任伯年迁居苏州,光绪八年(1882)并由友人荐作“作贰小吏”。他们的初次见面当是他们客居苏州的这段日子。有资料称1883年春天吴昌硕慕名趋府拜望海派书画翘楚任伯年,吴欲拜任为师。有资料称任见吴金石书法功力了得,颇激赏。这便是后世所谓“互为师友”一说的由来。作为二人知交见证,任伯年为吴昌硕画过多幅肖像,传世的先后有《芜菁亭长小像》《棕荫纳凉图》《酸寒尉像》等。《酸寒尉像》图虽是后作,草草逸笔,唯图一人,不似另外两幅皆有景物烘托、内容丰富,然能以后胜先,以少胜多唯“传神”二字可以解释《酸寒尉像》图的魅力。吴昌硕当时“作贰小吏”种种心态毕肖于现,加上画家以官服马褂图其貌样,应该画的是初次见面时的情状。作为职业画家任伯年默记默写功夫,不因时光流逝而淡忘,却由惊鸿一瞥而精彩。技近乎道的中国画独特造型语言,直可与西画比肩的绝佳案例。
当代坊间对任、吴关系有颠倒之说,不少人认为吴缶老成就在任伯年之上。一些公允之说也是称二人难分轩轾。难分未必不能分。众说纷纭的原因,摒弃艺术本身,主要还是后生几年的吴昌硕比任伯年多活了几十年,又有王一亭、齐白石等学生有意无意间为其抬轿子,声誉日隆也就不奇怪了。中国文化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我们更不必纠结应该给任吴二人区分金银。任、吴二人高山流水之谊是一段“海上画派”佳话。任伯年去世时,吴昌硕撰祭联:“画笔千秋名,汉石隋泥同不朽;临风百回哭,水痕墨气失知音。”当事人为两人关系早已作了盖棺定论。
回到《酸寒尉像》图本身,浙江乡贤杨岘老人的长题也不可不补记一笔:“何人画此酸寒尉,冠盖丛中愁不类。苍茫独立意何营,似欲吟诗艰一字。……”至此《酸寒尉像》解读差可告一段落,以下皆可谓题外话。
本书再版有炒冷饭之嫌,只是在十几年前出版的原书基础上加了新序和几篇延伸阅读。唯一增加的内容就是任伯年这张《酸寒尉像》。中国画人物画对“传神”的强调带有很浓的中国式品味和特质。即并不特别强调精细地观察与解剖客观对象,而是把观察感受的表现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同时又举重若轻地似乎是不经意间完成这一切。这和强调数学般准确与理性精神的西方由希腊艺术至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脉相承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区别。
任伯年生活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是新时代到来前的风雷激荡,也是旧山河破碎中的风雨飘摇。而作为创造经典艺术家,无论他表现是什么,一定会留下时代的刻痕。人物画在这一方面更有其直观敏感同时又深刻凝重的特殊性。创作中的艺术家和表现对象之间一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后世的解读又使之超越时空进入多维存在。中国画消亡是必然的,中国画精神是永恒的 。《酸寒尉像》图化古为今,虽是为一人造像,涵盖的却是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缩影。统观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遗存无不例外皆有此两大特质。
今天看来,中国画经典构成的两大要素即历史感和时代性。历史感可以用有古意来指称,而时代性则是艺术家的作品能否发时代之音。为时代立言可以是高居庙堂的黄钟大吕,也不排斥坊间草间之不绝虫鸣。余将中国画思想归纳为新六法:形为体,诗为魂,笔为主,墨为臣,色为花,气为命。如此观照《酸寒尉像》图。
任伯年有开风气之新和个性语言特色,然不失源头活水之赓续;能图心底寒怆仍保有风雅戏谑之畅快。任伯年生活的时代已成往事,选择中国近现代风雷激荡潮流中表现一位小人物肖像的《酸寒尉像》也许是画家惟精惟淳,醉心画事的不经意所为,而用它来为两千年中国画划上句号,却是我慎重考量。尚祈诸君明鉴。
责任编辑:晨风
当代艺术家官网
www.arts168.com
- 上一个:刘传铭:《从马王堆到上海滩——中国画两千年》 章节提要
- 下一个: 王熙炯:鬼才老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