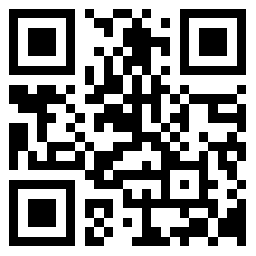艺术论坛
《自游 · 自由》(代序)
一切如仪顺利进行的活动现场,在获聘“法中联谊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时, 欧洲科学院院士、联谊会会长毕征庆邀我上台演讲。
此刻讲话当然未能免俗地回顾历史,申述了中法文明交流的伟大友谊。记得 结束讲话前,我提到了当年 4 ·15 巴黎圣母院那场灾难性大火。认为那是刻在美 丽巴黎和世界文明脸上的一道伤疤,我祈祷修复圣母院的工作尽快展开。
就在刚才,2024 年 12 月 8 日清晨我从网上看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圣 母院修复竣工典礼上的讲话:“我们可能再也听不到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了……而 如今,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再次响起…… ”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动,这大概就是苦难 与重生那文明交叠前行的脚步伴着钟声踏响的节拍。
历史无言,脚步有声。对脚步敏感即是对人生敏感, 有可能会是一个拥有行 旅灵魂的流浪汉。可又有几人能体味流浪汉行囊里背负的正是无家可归之乡愁。
我五年前出版的《沉思如舞》一书中写出了《背起故乡的流浪》
故乡情是一首老掉牙白了头驼着背哑了声的老歌。
前有范仲淹“去国怀乡 ”之浩叹,后有余光中“一枚小小邮票 ”之轻吟。
在古今中外无数诗人文人的口中,故乡被嚼烂了、打碎了、榨干了、毁灭了。 无数次起心动念想写一写故乡、哼一哼这首老歌,但又无数次加一次地放弃。何 况现在只要打开电视就不时会听到“一碗水,一杯酒,一生情 ”那苍白无魂故作 深情的表白,就更断了念想,甚至一想到故乡这个话题都觉得从里到外冒着俗气。
说断了念想本身也还是一种念想,诚如绝望是最深最痛的希望,既然躲不过 去,那就只好屈服。
李白登黄鹤楼时感触,“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也是一种屈服, 但终究还是未能放弃写诗。
亲情、爱情、乡情,大概是个体生命体验刻骨铭心的三种情,至于朋友情、 师生情、同学情、国家情、艺术情、事业情等等都像兑了水的酒、放了添加剂的 食物,到最后还是会洞见底色,回归这与生俱来的“三情 ”。当我们从生于故乡、 离开故乡、思念故乡、遥望故乡的匆匆脚步中读出故乡已回不去的时候, 敏感的 诗心会发现自己的况味人生不过是在背着故乡的流浪。
“叶落终归根,狐死必首丘 ”的过往悲鸣还不是最惨,更惨的是现在人人已 无乡可近,无家可回。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有一篇《乡路上的唢呐》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 大地 ” 副刊上,喜悦至今记忆犹新。我一直将这小小的得意珍藏在心底,并视之为铭言 的起点。
后来读《史记 ·项羽本纪》知道这位目空四海的西楚霸王也有“ 富贵不还乡, 如锦衣夜行 ”的故园情。
盖世英雄也是平常人。无论悲喜, 只有和乡人分享才是真的有滋有味。项羽 一炬火烧咸阳后回没回故乡《史记》没记。所以人情浓淡、世事无常的乡情变味, 楚霸王无法体会。他那万丈豪迈的乡愿终非是乡情的全部。
唐朝禅宗高僧马祖道一的故事给项羽做了补充。
马祖道一是什邡人,成大师后回故里,乡人争着一睹大师风采。冷不防一个溪边淘米的老婆婆看了一眼起哄的“马粉 ”说,哪里来的大师,这不是马簸箕家 的二愣子吗?马大师气泄叹出:
今天看来项羽的衣锦还乡,马祖的道成名扬还是浅薄。没有经历过无数次望 乡恋乡还乡探乡,又无数次“不还总思乡,还乡不见乡 ”的失望酸楚和永远回不 去故乡的绝望是没有资格谈故乡的。
传铭出生于江淮古庐州的合肥,这个不土不洋不东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的 小城,初解放时 5 万人口 12 平方公里属地。怎么也不能想到,现在已经是妄图 和首都北京魔都上海比肩近千万人口的“霸都 ”。但没有了“一人巷二郎庙三孝 口四牌楼五星寺六谷祠七星街八蜡祠九狮桥十字街 ”的合肥还叫合肥吗?没有 了逍遥津的邃庄品茶、包河畔的撑荷剥莲、凤凰桥的神话故事、雨花塘的夏日垂 钓,还能叫合肥吗?没有了刘鸿盛的馄饨、绿杨村的排骨、官德桥的烧饼、三河 镇的米饺、大窑湾的白米虾、肥东肥西的老母鸡汤, 还会有乡味吗?没有上派河 大嫂的机滋不分,没有店埠街老叔的“真得味”还会有乡音吗?
合肥在大湖名城的发展中一路狂奔,而故乡在传铭的心中早死了。
我承认,关于乡愁的新旧诗大多是在“少年不识愁滋味 ”的时候谈的,是在 不知痛的麻木和美感玩味的少不更事糊涂里读的,以为这一切都是古人老人的事。 而给我这道一直存在一直新鲜的伤口撒上一把盐,让我感到冰冷刺痛的却是在世 界文坛无足轻重的日本现代文学。
甚至也不是夏目漱石、二叶亭四谜、小林多喜二、川端康成这些日本文坛的 泰山北斗,而是和我同龄的村上春树和一群并不知名日本作家们的关于日本二战 后经济飞速发展现代化进程中的迷惘与失落。是对现代都市化中消失的村庄和回 不去故乡的一代人绝望。他们的愤懑与痛苦仿佛是一根根毒针刺进了我的灵魂,
让我不得不和他们一起沉思,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庆幸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失去故乡引来的追问虽然沉重, 阴郁却应 摆脱。因为只有穿过“挪威的森林”才能看到更多的风景,才能“且听风吟 ”, 才能不忘再潦倒的流浪汉也应该是一个人而非丧家犬。
对于个体而言,生命只是一次或长或短的“自游”。怀念故乡是怀念那个懵 懂少年时代的人和事。那是和泥土、父母、山川、湖泊捆绑在一起的不变记忆。 然而失去故乡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渴望诗与远方是人的基因,乡愁乡恋 是一个悖论。其实人有两个故乡,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屋老街老城,另一个在 心之向往心之安处的远方,它的名字叫“自由”。它在不少人的逆旅人生路上一直 在变化在被寻找被发现……
成立于 1922 年 12 月 30 日解体于 1991 年 12 月 26 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曾经是“老大哥”的家,也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梦中家园。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土豆烧牛肉、面包鱼子酱, 这些对生活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 60 年代极 端贫困饥饿那一代人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对我而言, 还要加上苏联前身俄罗斯 的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 列夫 ·托尔斯泰、格林卡、柴可夫斯 基、列宾、列维坦……他们那些表现人性与神性,爱情与背叛,浪漫与青春,阴 霾与阳光的文学艺术,加上一些被我生吞活剥咽下去的“别车杜”……生活寒酸、 物质贫乏,但又精神丰富、充满幻想, 在这古今两靠岸、中西混杂中, 一颗晶莹 的种子根植在一位少不更事少年的心田,最终我被塑造成了一个平民思想和贵族 精神的矛盾结合体。
按时间顺序,我的欧洲情结是启始于苏联,这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苏联也有 欧洲情结。尽管它的国土面积大部分在亚洲, 但它一直面向西方,以欧洲国家自 视。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概念而论它不是一个国家,而 是一个合作组织一个利益共同体,时髦的说法是命运共同体。可它偏偏就是一个 国家。一个可以和整个西方世界叫板的庞然大物。上世纪末它轰然崩溃倒塌, 成 了像恐龙一样的过去时存在。我震惊,但却丝毫不惋惜。因为明白了我曾经看到的一切繁华和诗意只不过是被铁幕掩盖的表象。一个不愿在伏特加和葡萄酒中沉 沦的灵魂睁开了眼睛又一次出发。这一次跋山涉水寻找精神故乡已多了几分理性。
崇洋不媚外、出家不离家,其中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复杂与微妙不足为外人道。 多年以后,《在沉思如舞》一书中那篇《不要在一杯葡萄酒中沉沦》透露的正是 这斑剥的况味。
不要以为我是要和你们讨论葡萄酒和流浪;
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劝你们不要在一杯葡萄酒中流浪而是去一碗女儿红中醉 卧;更不要以为我是要吐槽葡萄酒而公开颂扬非葡萄酒的酒。
也就这么一说,都怪葡萄酒自己不小心撞到了我这杆老烟枪的枪口。
什么时候有酒?什么时候有葡萄酒?什么时候中国有葡萄酒?这在历史学 家“名物考”那里都是严肃的学术问题。当代中国多的是这一类历史学家,他们 确实一个比一个严肃,又一个比一个学术。不过历史学的殿堂和历史的天空如果 都靠这样的严肃学术来支撑的话,奉劝同志们还是早早离开这类严肃的学术,而 去看那红绿晃荡的穿越剧,至少那些戏说没有故作高深,严肃的面孔上涂的是一 抹令人可以发笑的油彩。
这些问题在我这里就很简单,王翰的一句“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催 ”让我认定葡萄酒是大唐王朝的可口可乐,是唐诗的酵母,是李太白的催命符 和杜工部的流浪债,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撒马尔罕传来的妖姬。
由于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丝绸之路近年来从交通史的冷板凳上一下子跳 起来,成了全民热议的公共话题。于是美国汉学家谢弗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 就一版再版地从《唐代外来文明》到《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再到《撒马尔罕的金 桃》,花样翻新的瓶子里装的还是那一种老葡萄酒。总之,它成了一部畅销书。 出版商嗅觉灵敏功不可没。
我一边后悔上当买了不同版本的同一本书,但还是喜欢这本书。因为它严肃 地证明了铭言非胡说。
这本书的第 311 页上还引用了韩愈谴责一位衰落破败的葡萄园主的诗:
如果说舶来品葡萄酒是一种象征的话,那么洋鬼子的心思实在太毒了。它让 我们“将进酒,杯莫停 ”,让天朝自嗨,一个劲地把自己灌得晕晕乎乎,还且还 上瘾,一醉千年。
近些年富起的国人酒瘾更疯狂,已经不满足玉碗盛来那一点点琥珀光,而是 漂洋过海买酒庄。出手之阔绰把洋鬼子吓了一跳。买就买吧, 我们人虽穷却也不 眼红。可这些人偏偏要标榜自己有品位, 好像喝红酒比喝白酒,喝葡萄酒比喝二 锅头高贵,就是北京人说的能装逼和上海人说的有腔调。这我就实在坐不住了。 我不得不说,你就是再有钱也不过是在一杯葡萄酒里流浪的穷鬼,洋人未必就会 买你的账!他们不在心里笑话你是銭多人傻的傻逼,已经是基督教遗传的仁慈了。
眼下和自大狂孪生的崇洋病当然不仅仅是迷恋一杯葡萄酒。
移民潮、出国热、留学热就是一种另类的醉酒疯病。其间虽有一些跟风的浅 薄和不必要的担忧,望子成龙的可怜父母心。然说到底其中大多数还是在耍一点 中国式的小聪明。既要沾伟大祖国的光, 又要骂黄土地的娘,同时还要占“阿妈 瑞克 ”的便宜。机关算尽太聪明, 就是忘了“ 葡萄酒不能当水喝 ”这样一个朴素 的真理,人要活着还是要喝水。
算了,就让那些愿意在一杯葡萄酒中流浪汉流浪吧,这些人留下来最多也只 能在不是葡萄酒伏特加或各种花样翻新的酒中沉沦吧。
这些文字讨论的当然不仅仅是选择喝什么酒,是关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既然故国故乡无法选择也不能讨论,那就将目光转向欧洲,转向我曾经一直坚信的“文明的中心”。
关于“文明中心说”,考古学尺子是时间长短,科学家考量生态好坏,经济 学标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次,政治聚焦制度优劣。这些问题都不适合成 为公共话题,更不适合一本正经地跨界讨论,同时也非我所能非我所愿。我只 关心文化形态多样性,生命选择自由度。
本书给出的答案仅是几次欧洲“自由行”散记,目之所及笔之所记的快递 “非营养快餐”说了几句实话而已。不要以为我妄自菲薄,说实话需要勇敢, 半个多世纪努力磨砺我才学会了“说实话”这三个字。本书当然不止说实话。
2020 年以来,世界好像依然故我地热闹。但我还是下意识地体会到后疫情 时代的寒意。但说实话是认识真实的世界第一步。
有一个不少人熟悉的小故事。荣格漫步在湖边驻足时低头看见了因风皱面 的水中一个人变形扭曲丑陋的倒影,更惊讶地发现了这正是另一个自己。这一 切让他不安。他不觉倒退一步,这时听到了影子低沉的声音:“我是你阴影,为 什么要逃避?”声音让他停下来,荣格静静坐下与影子对视。影子又说:“接纳 我,你才能完整。”荣格若有所悟,喃喃回答:“我承认你是恐惧不安和隐秘欲 望中的我。”湖面复归平静,荣格复归清明。他后来写出了“接纳自己的缺陷, 才能发现真正的自己”。沿着此一思路想下去,应该是看见理想的荒芜,才能看 见真实的世界与荒诞。
自游和自由同音同义,然分属不同层面。自游指行动,自由指思想,两者 又有一定内在联系。一般意义上的自游指一个人想去哪儿抬腿可走,想吃什么 张口即来。至于国际旅行不受限,一本护照在手,到处皆可“PASS”。如此, 自 游便和自由重叠了,不再只是一个谐音梗游戏。
2017 年台湾已变蓝为绿,然大陆赴台游热度无明显降温。近千万大陆客被 台湾方面拒签的仅有两人中敝人就是一个。原因要从两年前说起。2015 年 5 月20 日前,台湾是国民党马英九执政。也是两岸关系热热闹闹的“蜜月期 ”。我 因赴台参加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 ”《于右任》纪录片开机礼于三月底赴台。 此刻距离台湾由蓝变绿的 5 ·20 不足两个月,政治上当然是个“敏感期 ”。故 原定的大陆方面相关领导无法成行。抵台后的一切活动便由我这个“总撰稿人 ”出席来支撑场面。因为我是单独从上海出发办的是“旅游签证 ”,按台湾 规定参加任何非旅游活动即违规,何况我在开幕仪式上演讲,后来又接受媒体 采访,都被台方记录在档,这就是后来的拒签理由。台湾我去过多次,一次被 拒签当然恼火,但未过分在意,只是写了几句感叹“自由”归零的牢骚话。
自游和自由不尽相同。自游简单,自由复杂。在各种阐释自由的哲思中,康德那句“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
候,能不干什么。”深刻地揭示自由的本质。我将之译成“无所不能而有所不为 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赞同的思想。
萧伯纳那句“自由意味着责任,这也许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害怕它的原因”就难以理解一些。后经维特斯根坦“天才之为责任” 的一句话解读才使我 们释然,原来对自由漠然的人会是害怕担当社会责任怯懦的人。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无名氏那句话,“我野蛮生长,自己便是月亮”。不着 一字尽得风流。没有解读自由却将获得自由的唯一条件说明白了,将获得诗与 理想的条件说明了。必须强调的是自然生态下才会“野蛮生长 ”,人工设计的那 些天花乱坠吹捧的制度不包括自由。
刘传铭/文
![]()
一切如仪顺利进行的活动现场,在获聘“法中联谊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时, 欧洲科学院院士、联谊会会长毕征庆邀我上台演讲。
此刻讲话当然未能免俗地回顾历史,申述了中法文明交流的伟大友谊。记得 结束讲话前,我提到了当年 4 ·15 巴黎圣母院那场灾难性大火。认为那是刻在美 丽巴黎和世界文明脸上的一道伤疤,我祈祷修复圣母院的工作尽快展开。
就在刚才,2024 年 12 月 8 日清晨我从网上看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圣 母院修复竣工典礼上的讲话:“我们可能再也听不到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了……而 如今,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再次响起…… ”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动,这大概就是苦难 与重生那文明交叠前行的脚步伴着钟声踏响的节拍。
历史无言,脚步有声。对脚步敏感即是对人生敏感, 有可能会是一个拥有行 旅灵魂的流浪汉。可又有几人能体味流浪汉行囊里背负的正是无家可归之乡愁。
我五年前出版的《沉思如舞》一书中写出了《背起故乡的流浪》
故乡情是一首老掉牙白了头驼着背哑了声的老歌。
前有范仲淹“去国怀乡 ”之浩叹,后有余光中“一枚小小邮票 ”之轻吟。
在古今中外无数诗人文人的口中,故乡被嚼烂了、打碎了、榨干了、毁灭了。 无数次起心动念想写一写故乡、哼一哼这首老歌,但又无数次加一次地放弃。何 况现在只要打开电视就不时会听到“一碗水,一杯酒,一生情 ”那苍白无魂故作 深情的表白,就更断了念想,甚至一想到故乡这个话题都觉得从里到外冒着俗气。
说断了念想本身也还是一种念想,诚如绝望是最深最痛的希望,既然躲不过 去,那就只好屈服。
李白登黄鹤楼时感触,“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也是一种屈服, 但终究还是未能放弃写诗。
亲情、爱情、乡情,大概是个体生命体验刻骨铭心的三种情,至于朋友情、 师生情、同学情、国家情、艺术情、事业情等等都像兑了水的酒、放了添加剂的 食物,到最后还是会洞见底色,回归这与生俱来的“三情 ”。当我们从生于故乡、 离开故乡、思念故乡、遥望故乡的匆匆脚步中读出故乡已回不去的时候, 敏感的 诗心会发现自己的况味人生不过是在背着故乡的流浪。
“叶落终归根,狐死必首丘 ”的过往悲鸣还不是最惨,更惨的是现在人人已 无乡可近,无家可回。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有一篇《乡路上的唢呐》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 大地 ” 副刊上,喜悦至今记忆犹新。我一直将这小小的得意珍藏在心底,并视之为铭言 的起点。
后来读《史记 ·项羽本纪》知道这位目空四海的西楚霸王也有“ 富贵不还乡, 如锦衣夜行 ”的故园情。
盖世英雄也是平常人。无论悲喜, 只有和乡人分享才是真的有滋有味。项羽 一炬火烧咸阳后回没回故乡《史记》没记。所以人情浓淡、世事无常的乡情变味, 楚霸王无法体会。他那万丈豪迈的乡愿终非是乡情的全部。
唐朝禅宗高僧马祖道一的故事给项羽做了补充。
马祖道一是什邡人,成大师后回故里,乡人争着一睹大师风采。冷不防一个溪边淘米的老婆婆看了一眼起哄的“马粉 ”说,哪里来的大师,这不是马簸箕家 的二愣子吗?马大师气泄叹出:
为道莫还乡,游乡道不成。
溪边老婆子,呼我旧时名。
一叫小名,立马笑场。从此马祖再也没回过故乡。今天看来项羽的衣锦还乡,马祖的道成名扬还是浅薄。没有经历过无数次望 乡恋乡还乡探乡,又无数次“不还总思乡,还乡不见乡 ”的失望酸楚和永远回不 去故乡的绝望是没有资格谈故乡的。
传铭出生于江淮古庐州的合肥,这个不土不洋不东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的 小城,初解放时 5 万人口 12 平方公里属地。怎么也不能想到,现在已经是妄图 和首都北京魔都上海比肩近千万人口的“霸都 ”。但没有了“一人巷二郎庙三孝 口四牌楼五星寺六谷祠七星街八蜡祠九狮桥十字街 ”的合肥还叫合肥吗?没有 了逍遥津的邃庄品茶、包河畔的撑荷剥莲、凤凰桥的神话故事、雨花塘的夏日垂 钓,还能叫合肥吗?没有了刘鸿盛的馄饨、绿杨村的排骨、官德桥的烧饼、三河 镇的米饺、大窑湾的白米虾、肥东肥西的老母鸡汤, 还会有乡味吗?没有上派河 大嫂的机滋不分,没有店埠街老叔的“真得味”还会有乡音吗?
合肥在大湖名城的发展中一路狂奔,而故乡在传铭的心中早死了。
我承认,关于乡愁的新旧诗大多是在“少年不识愁滋味 ”的时候谈的,是在 不知痛的麻木和美感玩味的少不更事糊涂里读的,以为这一切都是古人老人的事。 而给我这道一直存在一直新鲜的伤口撒上一把盐,让我感到冰冷刺痛的却是在世 界文坛无足轻重的日本现代文学。
甚至也不是夏目漱石、二叶亭四谜、小林多喜二、川端康成这些日本文坛的 泰山北斗,而是和我同龄的村上春树和一群并不知名日本作家们的关于日本二战 后经济飞速发展现代化进程中的迷惘与失落。是对现代都市化中消失的村庄和回 不去故乡的一代人绝望。他们的愤懑与痛苦仿佛是一根根毒针刺进了我的灵魂,
让我不得不和他们一起沉思,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庆幸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失去故乡引来的追问虽然沉重, 阴郁却应 摆脱。因为只有穿过“挪威的森林”才能看到更多的风景,才能“且听风吟 ”, 才能不忘再潦倒的流浪汉也应该是一个人而非丧家犬。
对于个体而言,生命只是一次或长或短的“自游”。怀念故乡是怀念那个懵 懂少年时代的人和事。那是和泥土、父母、山川、湖泊捆绑在一起的不变记忆。 然而失去故乡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渴望诗与远方是人的基因,乡愁乡恋 是一个悖论。其实人有两个故乡,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屋老街老城,另一个在 心之向往心之安处的远方,它的名字叫“自由”。它在不少人的逆旅人生路上一直 在变化在被寻找被发现……
成立于 1922 年 12 月 30 日解体于 1991 年 12 月 26 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曾经是“老大哥”的家,也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梦中家园。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土豆烧牛肉、面包鱼子酱, 这些对生活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 60 年代极 端贫困饥饿那一代人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对我而言, 还要加上苏联前身俄罗斯 的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 列夫 ·托尔斯泰、格林卡、柴可夫斯 基、列宾、列维坦……他们那些表现人性与神性,爱情与背叛,浪漫与青春,阴 霾与阳光的文学艺术,加上一些被我生吞活剥咽下去的“别车杜”……生活寒酸、 物质贫乏,但又精神丰富、充满幻想, 在这古今两靠岸、中西混杂中, 一颗晶莹 的种子根植在一位少不更事少年的心田,最终我被塑造成了一个平民思想和贵族 精神的矛盾结合体。
按时间顺序,我的欧洲情结是启始于苏联,这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苏联也有 欧洲情结。尽管它的国土面积大部分在亚洲, 但它一直面向西方,以欧洲国家自 视。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概念而论它不是一个国家,而 是一个合作组织一个利益共同体,时髦的说法是命运共同体。可它偏偏就是一个 国家。一个可以和整个西方世界叫板的庞然大物。上世纪末它轰然崩溃倒塌, 成 了像恐龙一样的过去时存在。我震惊,但却丝毫不惋惜。因为明白了我曾经看到的一切繁华和诗意只不过是被铁幕掩盖的表象。一个不愿在伏特加和葡萄酒中沉 沦的灵魂睁开了眼睛又一次出发。这一次跋山涉水寻找精神故乡已多了几分理性。
崇洋不媚外、出家不离家,其中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复杂与微妙不足为外人道。 多年以后,《在沉思如舞》一书中那篇《不要在一杯葡萄酒中沉沦》透露的正是 这斑剥的况味。
不要以为我是要和你们讨论葡萄酒和流浪;
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劝你们不要在一杯葡萄酒中流浪而是去一碗女儿红中醉 卧;更不要以为我是要吐槽葡萄酒而公开颂扬非葡萄酒的酒。
也就这么一说,都怪葡萄酒自己不小心撞到了我这杆老烟枪的枪口。
什么时候有酒?什么时候有葡萄酒?什么时候中国有葡萄酒?这在历史学 家“名物考”那里都是严肃的学术问题。当代中国多的是这一类历史学家,他们 确实一个比一个严肃,又一个比一个学术。不过历史学的殿堂和历史的天空如果 都靠这样的严肃学术来支撑的话,奉劝同志们还是早早离开这类严肃的学术,而 去看那红绿晃荡的穿越剧,至少那些戏说没有故作高深,严肃的面孔上涂的是一 抹令人可以发笑的油彩。
这些问题在我这里就很简单,王翰的一句“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催 ”让我认定葡萄酒是大唐王朝的可口可乐,是唐诗的酵母,是李太白的催命符 和杜工部的流浪债,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撒马尔罕传来的妖姬。
由于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丝绸之路近年来从交通史的冷板凳上一下子跳 起来,成了全民热议的公共话题。于是美国汉学家谢弗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 就一版再版地从《唐代外来文明》到《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再到《撒马尔罕的金 桃》,花样翻新的瓶子里装的还是那一种老葡萄酒。总之,它成了一部畅销书。 出版商嗅觉灵敏功不可没。
我一边后悔上当买了不同版本的同一本书,但还是喜欢这本书。因为它严肃 地证明了铭言非胡说。
这本书的第 311 页上还引用了韩愈谴责一位衰落破败的葡萄园主的诗: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
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
这更让人有意外之喜,对我正在关注的“唐宋八大家 ”研究不无小补。如果说舶来品葡萄酒是一种象征的话,那么洋鬼子的心思实在太毒了。它让 我们“将进酒,杯莫停 ”,让天朝自嗨,一个劲地把自己灌得晕晕乎乎,还且还 上瘾,一醉千年。
近些年富起的国人酒瘾更疯狂,已经不满足玉碗盛来那一点点琥珀光,而是 漂洋过海买酒庄。出手之阔绰把洋鬼子吓了一跳。买就买吧, 我们人虽穷却也不 眼红。可这些人偏偏要标榜自己有品位, 好像喝红酒比喝白酒,喝葡萄酒比喝二 锅头高贵,就是北京人说的能装逼和上海人说的有腔调。这我就实在坐不住了。 我不得不说,你就是再有钱也不过是在一杯葡萄酒里流浪的穷鬼,洋人未必就会 买你的账!他们不在心里笑话你是銭多人傻的傻逼,已经是基督教遗传的仁慈了。
眼下和自大狂孪生的崇洋病当然不仅仅是迷恋一杯葡萄酒。
移民潮、出国热、留学热就是一种另类的醉酒疯病。其间虽有一些跟风的浅 薄和不必要的担忧,望子成龙的可怜父母心。然说到底其中大多数还是在耍一点 中国式的小聪明。既要沾伟大祖国的光, 又要骂黄土地的娘,同时还要占“阿妈 瑞克 ”的便宜。机关算尽太聪明, 就是忘了“ 葡萄酒不能当水喝 ”这样一个朴素 的真理,人要活着还是要喝水。
算了,就让那些愿意在一杯葡萄酒中流浪汉流浪吧,这些人留下来最多也只 能在不是葡萄酒伏特加或各种花样翻新的酒中沉沦吧。
这些文字讨论的当然不仅仅是选择喝什么酒,是关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既然故国故乡无法选择也不能讨论,那就将目光转向欧洲,转向我曾经一直坚信的“文明的中心”。
关于“文明中心说”,考古学尺子是时间长短,科学家考量生态好坏,经济 学标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次,政治聚焦制度优劣。这些问题都不适合成 为公共话题,更不适合一本正经地跨界讨论,同时也非我所能非我所愿。我只 关心文化形态多样性,生命选择自由度。
本书给出的答案仅是几次欧洲“自由行”散记,目之所及笔之所记的快递 “非营养快餐”说了几句实话而已。不要以为我妄自菲薄,说实话需要勇敢, 半个多世纪努力磨砺我才学会了“说实话”这三个字。本书当然不止说实话。
2020 年以来,世界好像依然故我地热闹。但我还是下意识地体会到后疫情 时代的寒意。但说实话是认识真实的世界第一步。
有一个不少人熟悉的小故事。荣格漫步在湖边驻足时低头看见了因风皱面 的水中一个人变形扭曲丑陋的倒影,更惊讶地发现了这正是另一个自己。这一 切让他不安。他不觉倒退一步,这时听到了影子低沉的声音:“我是你阴影,为 什么要逃避?”声音让他停下来,荣格静静坐下与影子对视。影子又说:“接纳 我,你才能完整。”荣格若有所悟,喃喃回答:“我承认你是恐惧不安和隐秘欲 望中的我。”湖面复归平静,荣格复归清明。他后来写出了“接纳自己的缺陷, 才能发现真正的自己”。沿着此一思路想下去,应该是看见理想的荒芜,才能看 见真实的世界与荒诞。
自游和自由同音同义,然分属不同层面。自游指行动,自由指思想,两者 又有一定内在联系。一般意义上的自游指一个人想去哪儿抬腿可走,想吃什么 张口即来。至于国际旅行不受限,一本护照在手,到处皆可“PASS”。如此, 自 游便和自由重叠了,不再只是一个谐音梗游戏。
2017 年台湾已变蓝为绿,然大陆赴台游热度无明显降温。近千万大陆客被 台湾方面拒签的仅有两人中敝人就是一个。原因要从两年前说起。2015 年 5 月20 日前,台湾是国民党马英九执政。也是两岸关系热热闹闹的“蜜月期 ”。我 因赴台参加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 ”《于右任》纪录片开机礼于三月底赴台。 此刻距离台湾由蓝变绿的 5 ·20 不足两个月,政治上当然是个“敏感期 ”。故 原定的大陆方面相关领导无法成行。抵台后的一切活动便由我这个“总撰稿人 ”出席来支撑场面。因为我是单独从上海出发办的是“旅游签证 ”,按台湾 规定参加任何非旅游活动即违规,何况我在开幕仪式上演讲,后来又接受媒体 采访,都被台方记录在档,这就是后来的拒签理由。台湾我去过多次,一次被 拒签当然恼火,但未过分在意,只是写了几句感叹“自由”归零的牢骚话。
自游和自由不尽相同。自游简单,自由复杂。在各种阐释自由的哲思中,康德那句“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
候,能不干什么。”深刻地揭示自由的本质。我将之译成“无所不能而有所不为 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赞同的思想。
萧伯纳那句“自由意味着责任,这也许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害怕它的原因”就难以理解一些。后经维特斯根坦“天才之为责任” 的一句话解读才使我 们释然,原来对自由漠然的人会是害怕担当社会责任怯懦的人。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无名氏那句话,“我野蛮生长,自己便是月亮”。不着 一字尽得风流。没有解读自由却将获得自由的唯一条件说明白了,将获得诗与 理想的条件说明了。必须强调的是自然生态下才会“野蛮生长 ”,人工设计的那 些天花乱坠吹捧的制度不包括自由。
我庆幸,我是野生的。
2024 年 12 月 12 日于上海放鹤楼
==========================
注:作者刘传铭,著名国学家、学者、文艺史论家。
责任编辑:晨风
当代艺术家官网
www.art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