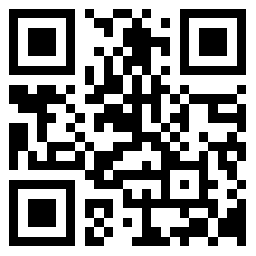艺术论坛
一张李可染的画
我曾买进卖出10次
■商勇(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商勇:Y先生对中国当今的一些著名鉴定家作何评价?
Y:大家对谢稚柳、徐邦达、启功这三人的侧重有所评价,他们各有所长,是我们尊重的前辈。鉴定这个行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好比警察破案,可能有一部分案件是破不了的,冤假错案也有的是。没有鉴定家是包治百病的,有也是瞎吹的。
比如某一个人对工笔一路的画特别明白,也有人对某一个时段里的十个八个画家简直清楚得不得了,他们的意见往往很重要。还有,裱画师傅的意见往往也很重要,例如,您问师傅,这张画您看看行不行?不行,这款儿挖过呀!您盯着款儿看,怎么看就是看不出来,没挖过呀?我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他其实不看款儿,他是看这画上有一块纸是白的,因为这儿的旧纸挪到挖款儿的位置上了,后来补上的纸比较新,所以是白的。他是这么看出来的。
一个真正搞鉴定的,我们先不谈搞古画鉴定的,那太复杂了,就谈近百年绘画的鉴定,我们真的要了解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作伪。我在上海还碰到过一位老先生,真是神了,他鉴定的时候不去看,而是拿手摸。我想,不可能啊,这不是胡诌吗?因为绘画是个平面的东西,不是立体造型,可以摸出这个鼻子高了,那个鼻子矮。后来我还真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什么道理?先举个例子,打麻将的人,打熟了的主儿,他不用看,拿手一摸就知道什么牌。他这个摸,是指感受画儿的包浆,后来我试了一下,果然感觉完全不一样,卷过10遍和卷过300遍的画,画背上的蜡,反复摩擦画面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绢本。另外纸本他也会摸,您说这是明朝的画,他还没全都打开看见款儿时,就在白纸上拿手捋,我正奇怪他捋什么呢?他就说:不对,这不是明朝的画,这是乾隆以后的。一看款儿,果然是乾隆以后的。这个也许不能作为科学的标准,但对一般的鉴定还是有意义的。最终确定下来,还要将裱工、纸张、题款、印鉴、绘画风格等综合起来看。
商勇:以前听人说徐邦达是“徐半尺”,他的“望气”是否也是看的纸张的包浆?
Y:不,他的“徐半尺”有个前提,就是必须有画,光有纸没画他也不行,必须有画面和露出一两个字的题跋。这一点我真是佩服他,一幅画刚一打开,露出一点画面和一两个字,他很快便说出这是谁的作品。比如四王,风格比较近似,但他能很快讲出这是王石谷的画还是王原祁的画,就是对各人的微妙差别也了如指掌的。当然鉴定真伪是另外一回事情。
商勇:您在鉴定中似乎特别偏重图章这一环节,是否和您早年是做印鉴收藏有关?
Y:是的。比如之前我在上海看到一套李方赝的册页,画面很好,但印鉴似乎有些问题,于是我就放弃了。不过一直从印鉴上来分析一张画也会犯错误,有时一个画家在朋友家里,一个没有准备的场合,画写意的,完全是兴之所致,很快就能画完。但因为没带图章,于是就没打上印。那么给这位朋友以后,他可能觉得很遗憾——不完美呀,我就自己搞两个图章盖上吧。可能当时没有经济的考虑而是审美的考虑,但恰好导致这批画的图章是伪的。因此不能从图章伪来彻底推翻一件东西。但就生意或商业上而言,这个瑕疵确实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有时,会遇到黄宾虹的一些课徒稿,甚至是无款无印的。黄宾虹是位很勤奋的画家,一看到画册就会画上两张,而他的画上往往可能只写两三个字。说到黄宾虹,我又想到一个经历。广州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叫王贵忱,他有一套的。大概10多年前,我请教过他一次,他认识黄宾虹,与他曾有过一段交往。我问他:“王老,您觉得黄宾虹从哪个角度看是最准确的?”他说:“别看款儿,他的那种题字好模仿,能写像了。”“那怎么看呢?”“您看他的房子!”“他的房子有什么特点呢?”“他的房子是‘船’,会动的。如果这房子看上去摇动,那么就是他的东西,如果房子是趴那儿的,就不是他的了。”我后来看了,发现确实是这样的。他的房子实际就是几条线,而没有刻意地去画建筑物,是从画面里面的结构和层次来考虑的。最近三五年,作伪黄宾虹的人确实有一套,刚一出场,就彻底打趴了许多人,破了不少收藏家的法眼。一个新的面貌突然出现时,大家可能原谅它,在心理上比较宽容,觉得黄宾虹很有可能会画成这样。
商勇:您在经营时,碰到一个财大气粗,但一点都不懂的买家,这时您推荐一件好东西给他是否感觉糟蹋了?
Y:这个不能推荐好的,因为他完全不明白。但也不能给他假的,回头他必定找您麻烦。因为他不懂但边上总有懂的呀,今天不懂,明天说不定看懂了。我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一张画卖出去,但买主听人讲这张画是假的,于是他会给您留面子,虚构出一个经济上的理由来要求退画了。那么就不和他纠缠,退就退吧,也不会去扣他的钱。干这一行有时生气能把人气死。
商勇:据说您有个有趣的最高记录:一张李可染的画,前后买进卖出10次。
Y:有。当然有时并没有收钱,只是口头协议,但没收钱不代表没买下来。我最近卖出去的几张画今天正想把他买回来,卖的时候他还没给我钱,但不代表他没买。刚刚正跟他谈判,想再买回来,我和买主说了,每张画加1万5千元,一共7张。
有时假画在我手上过,当时因为眼力原因没看出是假的也就当真的卖出去了。有一张画还挺贵的,七八年前卖出去的,我最近在香港看到了。有一个人带我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说这人有一幅画想卖,带我过去看看。我一看这张山水,哎哟,这不是我卖出来的吗?我现在看出这张画是假的了。但这个人不是直接跟我买的,我当时是卖给一个画廊的,画廊又卖给他了,当然都是当真的卖的。我现在看这画时倒舒了一口凉气,这张画肯定不对呀。但我肯定这画是我出手的,因为裱工是我裱的,可以看出来的。我问他您卖多少钱呀?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挺贵的。他说您根据目前的市场出个价吧。我说当时您可能买得挺贵的,但您也知道目前市场比较低迷……他马上说,我知道,我肯定会赔一点钱什么的。后来我还是给了他几万又把它买回来了。我怕他说是假的再退给那家画廊,大家都很熟的。那张画现在还在店里搁着,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比如我之前提到的10年前买的80多万的那批“齐白石”,最近才以无底价拍了2.7万,硬亏了80万。但是这批假画是同时代的他的学生作的,不像现在的粗制滥造。为这个我一夜没睡好,感觉自己太笨了,怎么上这个大当。到现在卖画人和我还有来往,但我没有提过这件事。大家都是明白人嘛。
商勇: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古代的不少优秀作品虽然经历千年的转手但往往品相很好。历史选择与淘汰起了怎样的作用?
Y:我们常讲宋人画得好,其实只是讲的某几个留下来的具体的画作,整个宋代画得极俗极不上路子的画家也多着呢。明末清初的也不全是八大,当时画得比海派还甜俗的大有人在,只是被历史淘汰了。那么回头来看,比如八大的,也不全是好画,差的多着呢,只是淘汰了。真正的好作品绝对是密不示人的,因此留下来的作品全是优秀的。不优秀不重要的作品,张三给李四,李四觉得不好,再送给王五,王五家里条件不好,烟熏火燎的,然后因为缺钱时刚好卖给一土财主,结果这土财主又破产了,这样来回倒腾几十年,这画就全烂了。只有宫廷或是真正很稳健的官宦世家才沉淀了特别重要的东西,因此流传有序的往往都是好东西,因为历史会无情地淘汰许多东西。上次在上博看国宝展,看到崔白的一张《寒雀图》,崭新得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上博整年陈列的几张宋人小品也是新得让人难以置信。其实就是因为保存条件好,收藏的人太知道他的价值。打开的时候,绝对选择天气,选择人,一个脏乎乎的主儿来看画,他就不会给您看。”
后记:英国19世纪艺术评论家乔治·摩尔在《十九世纪绘画艺术》中有一段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收藏艺术品更为强烈的激情——而且,我还要补充的是,从不知道还有比这更美的激情。在所有的激情之中,它最纯粹。拥有这种激情的人是为国家还是为他自己收藏并不重要。”在与Y的交谈中,作者感知到什么是收藏家的激情和智慧;这激情是物品带来的知识和审美的激情,而智慧则是这个“水很深”的行当所蕴含的不可言说的大智和伦理。和这个藏家大鳄的交谈能使人感知到中国收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千年行规”的具体可感。“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收藏圈的最高境界便是一眼便能洞穿其中的物、其中的人和其中的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也许不在条分缕析的理性剖析里,而是在静穆不语,拈花一笑。
- 上一个:许德民:寻根中国抽象艺术
- 下一个:成锋:我看新一届书协主席苏士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