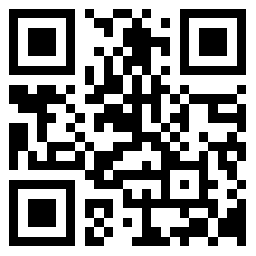艺术论坛
![]()
陈明哲
新徽派美术概论
陈明哲/文
艺术是发展的,艺术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尽管人们对艺术发展模式论的观点不尽相同,然而艺术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人们已有的共识。其中绘画艺术伴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绘画流派是绘画发展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不同的风格流派,这些不同的风格流派往往体现了绘画发展的规律性。历史上往往社会的大开放、大融合就会迎来艺术的大创造、大发展,表现在绘画上一定是百家林立,画派纷呈。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美术也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大美术时代,一个更多元、更包容、更开放,更自由的美术创作时代。世纪之交,作为文化大省的安徽提出“新徽派美术”发展战略,从艺术发展的模式论来讲,既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又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从 “新徽派美术” 的提出到今天已经是十多年过去了,“新徽派美术”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基于此,我们更应该把新徽派美术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学理依据、现实意义以及新徽派美术和新安画派、徽派版画、新徽派版画、黄山画派、徽文化、徽州学等诸多画派、学科的关系作进一步梳理。
一 关于新徽派美术几个关联词的概念
新徽派美术在今天有时约称为“新徽派”,单从字面上看它更像是“徽派”的延续,其实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画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只是当代安徽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品牌或一面旗帜。最早“新徽派”一词是专指“新徽派版画”。 起因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以赖少其为代表的安徽版画家们借鉴历史上徽派版画优秀传统经验,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版画,李桦和古元称之为“新徽派版画”。到了八九十年代赖少其为更好地发展安徽美术事业经常提到的“新徽派”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了,就不是仅仅限于版画画种,它可以放大到整个“美术”的概念上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新徽派美术”。
汉语中“美术”一词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开篇就讲到“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 art)。”中国古籍《考工记》、《论语》、《列子》只有“绘事”、“画绘”、“术艺”等词的出现,到汉代出现“艺术”一词。近代“美术”一词的引进,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它常和“艺术”互换使用,之后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艺术”和“美术”的概念才被逐渐分离开来。“美术恒以关系视觉美术为范围”,(蔡元培)这样“美术”概念的范畴就非常明确了。新徽派美术是涵盖以“视觉美术”的国画、版画、油画、雕塑等诸多艺术门类,所以它和中国画历史上画派的概念范畴不同。
谈到新徽派美术,它虽然和历史上的画派不同,但我们还是要先明确“画派”的概念。画派中的 “派”字本意最早在东汉许慎《说文》:派,别水也。西晋左思《吴都赋》又有“百川派别”句,刘逵为之注引最为明确:水别流为派。“派”字用在绘画这一领域时则说明绘画的繁荣已经像河流一样支系众多。“画派”之说肇于六朝。①所谓“画派”就是一些艺术见解、审美情趣、表现手法及创作风格接近的个体画家构成的群体。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讲到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吴道子分别代表当时绘画的疏体和密体两种风格流派,称为“疏密二体”,又在《论传授南北时代》的章节里讲“各有师资,递相仿效,或自开户牅,或未及门墙。”都提到当时绘画门派及师承问题。
“画派”一词则出现相对较晚,明代画家杜琼作长歌《东原集赠刘草窗画》有句“马夏铁骨自成体,不与此派相合比”,“诸公尽衍辋川派,余子纷纷不足推。”把古今画派的衍变一一道出。稍晚的何良俊在《四友斋画论》又有“夫画家各有传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种:赵松雪出于李龙眠,李龙眠出于顾恺之,此所谓铁线描;马和之、马远则出于吴道子,此所谓兰叶描也。”接着的莫是龙、董其昌分别其《画说》和《画禅室随笔》专门对历史上画派的研究,“画派”一词屡屡被提及。及至清代乾嘉时的张庚在《浦山论画》对各画派的源流及得失叙述地更为明确:“画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别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于戴进,成于蓝瑛。……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近代著名美术理论家俞剑华先生在《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对张庚《浦山论画》的这段话有专门的按语“明季清初各派名称,实始于此”。 ② “新安画派”的名称也是最早出现在这里,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谈新徽派美术的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徽派”的概念,“徽派”一词最早出现在郑振铎的著作中,他在《明代徽派的版画》中首倡“徽派”这一概念。徽派版画是明清之际活跃在皖南的画家和木刻艺人通力合作的艺术结晶,由于文人画家参于版画创作,使版画富有了文人书卷气,给中国传统版画艺术带来革新,也是徽派版画本身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二 新徽派美术产生的历史背景
有了对“美术” 、“画派”、 “徽派”和“新徽派”的认识,我们就能厘清新徽派美术并不等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画派,也不是历史上某一画派的简单延续,它是当代安徽美术的“一种自觉的推动,强化,形成”,(鲍加语)它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在以下几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1,新时期安徽美术战略发展的需要
二十世纪以来,百年中国画在争论中发展,各种新的绘画流派不断涌现:海上画派、岭南画派、京津画派、金陵画派、长安画派等,各画派的艺术风格地域特征非常明显。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便利的交通、发达的信息和不断壮大的美术院校也并没有完全打破绘画的地域疆界,绘画流派依然在传递、派生、发展甚至“打造”着。但是任何以个人名义打造的画派也将是昙花一现,因为这种打造的画派不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你打“冰雪派”,我打“黄土派”,他打“漓江派”,都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定位成画派创始人,说穿了是在扯大旗、立山头,这样的“画派”再多也只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虚假繁荣现象。
本着科学、谨慎的态度,安徽美术提出“新徽派美术”发展战略,是尊重历史、尊重省情,从安徽美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鲍加在《安徽美术五十年》里讲到:“按照赖少其当时设想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各类画种中倡导‘新徽派’地域性艺术,但是由于特殊历史条件限制,这种新的探索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响应。”1992年,赖少其与雷铎的谈话还提到“新徽派”美术的一些问题,可惜也没有深入下去。2000年,刘景龙讲过:“我省美术应打什么旗,倡什么口号,大家思考了很多年,都有不少好的见解。但总体而言,大家认为地域性特征的重要。”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如何保持自己的地域特色并彰显时代精神,安徽美术在“徽”字上做文章,“打好徽字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基于以上原因,在 2000年《世纪之交·安徽省美术发展研讨会》上“新徽派美术”一经正式提出、讨论,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新徽派美术的提出符合安徽的地域特征,符合安徽美术发展的历史状况和当时的现实情况,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如果说安徽历史上众多“画派”是长江、淮河、新安江等是一条条流动的河流,那么新徽派美术就是大的水系,以整个安徽文化为支撑的水系。从美术的战略发展来看,它又是一面旗帜,“旗帜就是凝聚力,就是创造力,就是艺术生产力。” ③旗帜就是方向,这样前进的道路就会更明确。
2,徽学的兴起
徽学的兴起,对安徽近现代美术研究领域的日益扩展和对安徽当代美术的创作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徽学是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一门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客观社会历史和现实文化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
徽学研究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宾老(黄宾虹)便提出“徽学”这一概括徽州文化研究的概念,足见他的远见卓识,而且明确表示要建立一个学科,以指明徽州文化研究的方向。这在当时提出这一概念,实在是一个有着深远意义的创见。”④1993年全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徽学的研究开始走向全国,徽学也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继敦煌学、藏学之后的三大显学之一。已故著名徽文化研究学者汪世清先生说:“宾老提出‘徽学’这一创见,至少有两个基础,一是对新安画派的深入探索必然要涉及徽州文化在发展中的诸多方面,二是对家乡的文物和文献的广泛搜集和交流”。
黄宾虹对徽学的研究不遗余力,连续发表了关于徽州美术的很多文章,推动了近现代安徽美术研究和创作的热潮。从1907年《宾虹羼抹·叙摹印》、1909年的《梅花古衲传》、1926年的《黄山画苑论略》、1935年的《新安派论略》、1939年的《黄山丹青志》、1940年的《渐江大师事迹轶闻》到1943年的《垢道人轶事·垢道人遗著》等。另外还有 1934 年郑振铎《明代徽派的版画》、1946年郑秉珊的《新安画派概况》、1933年汪采白的《新安画派》等等都围绕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安徽的美术创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明确的学术方向。
随着徽学兴起,仅就新安画派的研究而言,自张庚在《浦山论画》提出“新安画派”一词以来,新安画派在中国美术史的位置愈显重要,这得力于黄宾虹、汪世清等诸先生的研究成果。黄宾虹的《渐江大师事迹轶闻》、《释石溪事迹汇编》、《垢道人轶事》;汪世清的《弘济与弘仁》、《雪庄的黄海云舫图》、《程邃的萧然集》、《清初画苑八家画目系年》等,通过系列的个案研究,包括作者的家世、生卒、里籍、交游、师承,作品的风格、题材、年代、真伪、传承等,突破已有的认识,发现新得历史联系,得出了超越前人的见解和结果。比如汪世清先生的《新安画派的渊源》不但梳理清了新安画派的历史渊源,还谈到了新安画派的未来发展:“今而后,新安派之绘画必将继续发展下去,但如何发展?一言以蔽之,优良传统之继承而发扬光大也。何谓新安画派之优良传统?仅以画风而言,则清简淡远与伟峻沉厚之结合。其结合也,理论、方法、内容、形式,均将以时代精神与物质条件之变化而推陈出新。在此发展过程中,徽人可为此作贡献焉,皖人可为此作贡献焉,国人可为此作贡献焉。”⑤先生如此开放的胸怀,体现了当今大美术时代的开放精神。艺术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画派的发展,研究画派是为了认识艺术发展的规律,认清了艺术发展的规律才有利于制定新徽派美术的战略发展方向。
3,赖少其艺术定位的确立
赖少其继承和发扬了徽派版画和新安画派艺术遗产精华,他的版画和中国画创作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化针对性”,近年来他的艺术地位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
谢稚柳高度评价他的版画:“赖少其的版画,在技巧、风格上显示了它的独特性……它强烈地接近着中国绘画的铺陈结体,而在色调方面也结合了中国绘画的着色法与色彩的运用,可以说是结合中国绘画的形式,开创了版画史上前所未有的面目。因此,它给人的艺术感受,是富有现实意义而带有中国绘画气氛的别开生面的新颖风调。”在版画界赖少其作为新徽派版画开创者已成定论。他在中国画领域同样取得巨大的成功,“为黄宾虹之后的又一位山水画大师”,(赵朴初)随着近年对赖少其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赖少其的艺术地位在安徽美术史乃至中国美术史都举足轻重。近年在广州、合肥等多地展览、研讨会与会的美术界、文艺界专家、学者达成共识:赖少其不仅是新徽派版画的开创者,也是新徽派美术的代表人物。
以前有学者、画家把他定位为“新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唐云在《勇攀黄山天梯的人——谈赖少其及其艺术》和赵朴初在《赖少其书画集序》以及梅墨生都把赖少其称为“新黄山画派”执旗人。历史上“黄山画派”的争议一直存在,直到近些年“黄山画派”的不成立论基本被学术界认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新黄山画派”也就无从谈起了。
关于“黄山画派”最早倡言建立的有黄宾虹、贺天健、潘天寿三家,但他们的主张各自独立,也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在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三家的支持者各有所据,众说纷纭,一直未取得共同认识。黄宾虹的学生汪世清极力反对黄的“黄山画派”说。他在致潘振球的信中讲:“黄宾虹是把从唐薛稷、张志和直到清中叶的徽州画家和个别外郡画家,统统挂在黄山画家名下。这就意味着从七世纪开始,徽州地区便有了‘黄山画派’,很显然这决非历史事实。”⑥画派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实,画派的界定的命名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要以客观的地域、时代和风格几个方面为依据,而不是可以凭主观意愿随意确定的。贺天健把画黄山的画家都归为“黄山派”,已经失去画派的本意,潘天寿以石涛、梅清、程鸣、方以智为“黄山画派”,更是主观的任意拼凑。
既然历史上不存在“黄山画派”,那么把赖少其定位为“新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错误的,赖少其艺术的历史定位就要重新考量。2000年当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打好徽字牌,做好徽文章,建设安徽文化大省”的口号时,从新徽派美术的战略发展考虑,把赖少其定位为新徽派美术的代表人物是非常切合实际的。2005年在合肥落成的赖少其艺术馆的前言上写到“赖少其发展了‘新安画派’,开拓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徽派艺术,成为众所公认新徽派美术的创始人和安徽省书画界当之无愧的卓越代表和旗手。”
三 新徽派美术的学理依据
探究新徽派美术的学理依据,我们必须从新徽派美术的继承性和包容性两个方面进行,纵向和横向两种角度遵循历史原则和现实原则进行分析。
1,新徽派美术的继承性
艺术的发展过程其内在结构是有继承性的,这种继承性反应着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连续性,继承性客观地反映艺术创作的地域性,又体现了艺术风格的同一性,不同艺术家他们之间的风格区别再大,但是他们不自觉地受到他们所处时代、地域、民族、阶级的影响和制约,从而显示出艺术风格的同一性。所以新徽派美术的继承性最能体现它风格特点,他体现了新徽派美术的根源。
今天的大美术时代我们更要强调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再挖掘、再认识。新徽派美术有着厚重的文化土壤,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徽文化,新徽派美术中的‘徽’字是发展新徽派美术的关键词之一,强调徽文化恰恰是发展新徽派美术战略的优势所在,同时也体现了新徽派美术的历史传承性。在美术创作中“徽”元素的大量应用和深度挖掘不仅能丰富了新徽派美术的创造,彰显了新徽派美术的地域特色,更体现了新徽派美术文化传承的血脉关系。徽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内容广博、深邃,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大宝藏。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新徽派美术创作的丰厚营养。黄宾虹和赖少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新安画派的继承和徽文化的吸纳。
黄宾虹早在1935年发表的《新安派论略》就是一篇比较详实的专门研究新安画派的论著。他的绘画是从新安画派入手的,早年行力于李流芳、程邃、弘仁等,王伯敏说:“黄宾虹四十岁左右所画山水,都是受新安画派的影响”。黄宾虹的绘画在六十岁以前基本上都是以学习传统为主,他最终艺术成就和他对新安画派以及徽文化的深入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他在‘新安画派’冷峻的这个背景下,走出了一条浑厚华滋的道路,这给我们画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王永敬)
同样新安画派对赖少其的山水画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赖少其饱读新安画派原作,对程邃、戴本孝等潜心临摹,深入研究,他认为绘画的继承非常重要,“不学传统空唐突”。只有良好的继承,才能谈得上传承,才会有新的创造。赖少其留下了大量的临摹新安画派的作品,1982年在颐和园休养时还临摹了很多程邃和梅清的作品,现在陈列在合肥赖少其艺术馆。他在谈创作时写道:“我到了安徽,才发现明遗民程邃的乾笔渴墨之法,我对他佩服得真是五体投地,情不自禁地写下‘恨晚生三百年,不能拜其为师也’” 。赖少其对新安画派的研究、继承让他在美术创作中终身受用,也为他晚年的变法埋下了坚实的中国文化之根。方贤道在他的文章中对黄宾虹和赖少其对新安画派的继承与发展有过这样的评价:“自新安画派后的三百多年,继承新安画派传统,开拓新生面的现代画家前有黄宾虹后有赖少其,他们都具有艺术家独特的人格魅力,综合的文化素养,独到的艺术见解和创造力,是当之无愧的继承和发展新安画派的支柱和核心。”我们通过黄宾虹、赖少其这条主线来看,新徽派美术的继承性明确,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创造、各有发展。
新徽派美术的文化继承性不仅体现在对皖南徽州文化的继承,还反映在对皖北老庄文化的继承上。在今年9月合肥举办的“新徽派美术名家学术邀请展”上,王永敬就谈到“‘新徽派’不要忽略‘老庄文化’”。从老庄到玄学,从玄学到玄言诗到山水诗,从山水诗到山水画的萌芽、产生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老庄文化对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和后来的写意画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作用。中国画创作上常常提到的词语诸如:“解衣盘礴”、“得意忘形”、“天人合一”、“心手双畅”等无不体现了老庄文化所倡导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受老庄文化影响的萧龙士一生笔墨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朴实纯真的“中和之美”是其不变的本色,这种追真求朴的美学思想源于庄子的“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萧龙士以朴之心、朴之情、朴之笔、朴之墨,描绘时代的至真、至善、至美,以一种“墙角种菜作花看”的浪漫主义情怀把浓郁的乡土气息融入到高度精粹的文人画之中 ,给当代大写意花鸟画注入健康的生命力,使绘画艺术更贴近生活,更具时代精神和人为精神,并开创了江淮大写意画派,影响深远。关于萧龙士和江淮大写意画派笔者有专门文章论述,在这里不再展开。
2,新徽派美术的包容性
如果说新徽派美术的“徽”字体现了“新徽派”的继承性,强调安徽的地域特色,那么“新”字则体现了新徽派美术的包容性,强调的是大美术概念。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有了创造才会“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美术的概念也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的美术事业也越来越走向繁荣,美术的创造、服务、传播、消费形式、表现手法日益多样化,艺术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各画种的界限也越来越小,新的面貌也越来越多,形成中国画创作的多元格局,中国美术也进入大美术时代。
新徽派美术有以黄宾虹为先导性画家、赖少其为代表人物,不分画种、流派、年龄、性别的安徽艺术家组成的创作阵容,有黄宾虹“向世界伸开臂膀,准备和任何来者握手” ⑦和赖少其“我们不仅应向古人学习,也应向同代人学习,向全世界的同行学习。” ⑧这样开放的创作理念和国际化视野,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新徽派美术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同时也符合艺术多样性这一特征,现实世界本身有无限丰富的多样性,艺术家有各自的创作个性,加上欣赏者有审美需要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艺术的多样性。
艺术的多样性还体现了它自身的开放性品格。刘继潮在《研究、发展与建设、创新---突破百年中国画论争的定势》一文中讲:“笔墨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的品格。绘画史表明,笔墨能够吸纳、消化各种艺术营养,进而创造出具有当代性的新笔墨。”绘画的发展总是在新的创造中发展的,笔墨的生命总是要有新的因子吸收,“近亲繁殖”只能导致畸形艺术的产生。新徽派美术的开放性品格是建立在和各种文化交流、沟通上的。黄宾虹在谈中西绘画时总是以开放的姿态:“中西绘画通过空前的沟通,终于可以在一个共同的民主或民学的精神的旗帜下,沿着自然美、线条美的轨道趋同、互动、竞赛了。中国画家不可悲观,实在正可乐观,尤其文化艺术上大有努力的余地。”赖少其受黄宾虹的直接影响,更是“将如虫蚀木的传统线条笔法与源自印象主义的灿烂色彩经验融为一体,给现代中国画艺术中的文化折中主义开拓了更广阔的新的前景。”⑨薛永年在谈林存安的中国画创作时也讲到:“黄宾虹的绘画里的某些抽象因素,我们也是可以跟西画放在一起理解的,人类艺术是有共通点的。赖少其晚年画作绝对是神品,也是打通中西,不仅是在笔墨,还包括色彩使用、空间处理,完全是一片神形。”黄宾虹和赖少其对传统的继承是“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他们的创造并不仅仅是精神家园的守护,更是一生绘画理想的寄托,是海纳百川的胸襟,吸纳和消化了各种艺术营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成就一片天地。
四 新徽派美术的现实意义
当前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发展文化,资源优势都是被放在首要位置来考量。安徽的文化资源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有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老庄文化等区域文化;在绘画历史上有新安画派、姑熟画派、宣城画派、桐城画派、龙城画派等绘画流派,这些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都是发展新徽派美术的优势所在。同时整合文化资源,推出新徽派美术战略,对传承历史文脉、传递绘画精神和发展繁荣当代美术创作,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传承历史文脉
宋人邓椿在《画继》里说:“画者,文之极也。”,绘画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笔墨承载着文化,同样文化也通过笔墨在传承。中国画创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中国人习惯把观赏画称“读”,把作画叫“写”,绘画和文化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安徽的文化是灿烂的、丰厚的,它在其长期的发展中,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在安徽大地上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区域文化,其中徽州文化最具地域性特色,安徽文化发展提出了“打好徽字牌”的口号,安徽美术提出新徽派美术发展战略也是基于此。
就徽文化而言,无论是从史学、文学、人文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民俗、民风、宗教礼法的角度,徽文化都不愧为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它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历史上徽州文化有纷呈的学派与流派,内容也几乎涵括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而且传承有序,都具有标本性的意义,因此徽学能成为三大显学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新徽派美术的创作无论是从内容、形式、还是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其中徽元素的应用都是比比可见的,有内容上表现结构严谨、雕镂精湛的徽派建筑的;有形式上借鉴典雅静穆、气息浓厚徽派版画的;有表现手法上吸收极富装饰意味徽州“三雕”的……都体现了徽文化深邃的哲学意境和丰厚的人文精神。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推动了安徽美术创作的繁荣,同时新徽派美术的繁荣也促进了徽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在皖北以萧龙士为代表的大写意花鸟画家群体,那敦厚、清新、朴实画风更能体现皖北地域的老庄文化,那种中庸平和,不急不厉创作心态,那种浓郁的乡土气质息,无不透露出朴素的老庄文化和谐的时代精神。
2,传递绘画精神
中国画的绘画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宾虹讲:“艺术流传在精神,不在形貌,貌可学而至,精神由感悟而生。”历史上个绘画流派的传承也不仅仅是风格样式的传承,它是一种绘画精神在传递。虽然画家艺术风格的确立是绘画流派产生的前提,但绘画精神才是绘画流派的灵魂。就新安画派而言,从渐江的“学人”精神到黄宾虹的“民学”思想,再到赖少其的“木石”精神,它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新安画派的品格高度、精神力量在传递,它传递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崇尚内在美,主题是自由、向上。
提到渐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他是避世的、消极的,其实当我们从他的艺术追求去研究,就会发现他“戛戛独造”的独立意识和自由向上的“学人”精神。渐江的作品很多款识出现“学人”二字,也有研究者从“学人画”方面探讨,我们这里更侧重是他精神品格的探讨。《左传·昭公九年》最早出现“学人”一词,这里的“学人”指求学的人,任继愈主编的《佛教大辞典》对“学人”的解释:“学人,亦称学道人,禅宗称谓,指参禅学佛的人”。渐江自称“学人”,这两方面的意思也是兼而有之,这里所说的“学人”精神更多的是指他谦逊、狷介、刚直、坚韧、向上、高洁的精神品格。渐江有诗“疏树寒山澹远姿,明知自不合时宜。迂翁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他不努力追求合乎时宜的画风,而是崇尚倪瓒的“疏树寒山”,甚至要把他的画供起来“岁岁焚香”。在很多典籍中有渐江“跪观倪画”的轶事:“遇有当意者,则长跽谛视,声息俱屏,有客在旁不知,呼之饭食不应也。”吴之騵《桂雨堂文集》中也记载渐江“每至欣赏处,常屈膝曰:是不可亵玩。”这都说明渐江对艺术顶礼膜拜和执着追求。即便这样,渐江也没有局限于对倪瓒、对传统亦步亦趋地模仿,而是远接倪瓒的创造精神 “敢言天地是吾师”,终于在吴门、云间、娄东各派之外“自树标帜”,开新安一派。三百年后的黄宾虹不斤斤于新安画派的风格样式,而是继承渐江的“学人”精神,积学一生,终开自家面目,成为中国画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也把新安画派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黄宾虹开创性地提出“君学绘画”和“民学绘画”两个概念,在艺术创造中他极力倡导“民学”思想,他认为:“君学绘画为宗庙朝廷服务,为政治作宣扬”,这种带有功利性的创作往往难于发挥个性。民学重在精神,黄宾虹提倡的民学绘画在于追求精神的解放和创造的自由,也符合老庄思想。他讲:“将来的世界,一定无所谓中西画之别的。各人作品尽有不同,精神都是一致的。”绘画实践中他是身体力行的,不拘泥于绘画的形貌,大胆尝试,有时甚至玩起了“实验水墨”, 傅雷谈黄宾虹晚年的画时讲“纯用粗线,不见物象,似近于欧西立体、野兽二派。”
赖少其受黄宾虹的影响很大,在中国画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他认为:“我们不仅应向古人学习,也应该向同代人学习,向全世界的同行学习,向民间学习,向青年学习,只要自己的主场站得正,就不怕向别人学习。学习的结果,应该是使得中国画更加丰富、更加美。”这和黄宾虹“向世界伸开臂膀,准备和任何来者握手!”一样博大的胸怀和开放的思想。鲁迅在给赖少其的信中说:“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⑩赖少其将画室名为“一木一石之斋”,用以自励,他通过一木一石叠垒,不断攀登、勇于创新,终于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思潮形成完美的对接,他的作品笔墨雄浑、色彩绚丽,无论从形式的美感、笔墨的张力或是视觉的冲击力无不张扬着积极向上的“木石”精神。黄宾虹讲:“笔墨历古今而不变。”就是指的这种积极向上笔墨精神,也就是我们要代代传递的绘画精神。
3,繁荣美术创作
由于美术与社会生活联系的广泛性和美术创作的多样性,因此美术具有认知、教育、审美的社会功能,自美术的产生以来它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着,所以发展美术事业,促进、扩展美术的社会功能也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蔡元培不只一次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倡导新徽派美术的意义还在于繁荣和指导当代安徽的美术创作,明确安徽美术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多地帮助人们认识世界,陶冶情操,开拓文明,提高审美,完善人格,全面提高人的精神素质。随着安徽建设文化强省的决心和力度不断加大,“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成了战略发展的核心,因此繁荣当代安徽美术创作对建设安徽文化强省和加大安徽精神文明建设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代美术创作卷入商品流通领域,把精神产品商品化,导致绘画精神的缺失。笔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上的宗教化,政治化 ,商品化后,世俗的力量直接影响画家的创作,市场化的“雅俗共赏”也成了画家创作的借口,就出现了很多脱离生活,脱离自然,脱离本土坏境的作品,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倡导新徽派美术,重振安徽美术雄风显得更为迫切与必要。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重振徽派雄风”的,因为历史上“徽派”是一个相对固定在“徽派版画”这一领域的概念,不能和新徽派美术这个大美术概念相对应,“新徽派”和“徽派”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与“旧”的关系,历史上安徽美术领域巨匠层出,画派林立,不能仅仅用“徽派”来代替,所以我们谈发展安徽美术时,讲“重振徽派雄风”就不是很严谨了。
重振安徽美术,繁荣安徽美术创作还在于根植本土环境,彰显地域特色,提倡在文化大脉络上有价值创新。最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当前美术界的伪创新和假繁荣现象:空洞的大制作,满构图,曰“冲击力”,曰“实验水墨”;毫无根基的笔墨游戏,曰“新文人画”,曰“超大写意”;或一味追求质感的工笔;或烂堆狂抹的重彩等等,不是颓废、消极的人物,就是桌布、床单式的花鸟,抑或阴森、古怪的山水,这些作品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美术界的一个现象,一些人急功近利,以变异求发展,以狂怪求个性,打着创新的幌子,只在“形貌”上做文章,不说人文精神,就是简单的技法也缺少认真的锤炼。发展新徽派美术,我们要多从渐江、程邃、査士标、汪采白、黄宾虹、赖少其、萧龙士、王石岑、黄叶村等这些大家的作品中去寻找深层的文化积蕴和丰厚的人文精神。在谈到新徽派艺术如何去寻找突破口时,龙瑞在今年9月在合肥举办的“新徽派美术名家学术邀请展”上讲:“就我个人来看,在继承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做好创新是关键。具体来说,一定要对老徽派艺术的历史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有研究才能让新作品底蕴深厚,所以说新徽派一方面不能离开老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关照当下各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艺术的新活力与动力。”龙瑞提到的老徽派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他还是认为创作中继承传统的重要性。
当下新徽派美术画家群体在全国的美术创作队伍中有亮点,但整体面貌还不够突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一些老一辈画家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一个与时代脱节的面孔,缺少赖少其“衰年变法”的勇气和精神;一些中年画家不注重自然造化和生活历练,一味地追求创新、追求自家面目,作品中缺少情感的注入,最终出来的是矫揉造作、面目全非的“产品”;还有一些青年画家忽视对传统的学习,追风逐尚,不是“笔墨当随时代”,而是笔墨随时尚,甚至直接否定笔墨专玩制作的也大有人在。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新徽派美术主流的、积极的一面,他们以发展的、开放的、包容的心态根植传统文化去寻找自己的个性语言,丰富自己的笔墨内涵,在新徽派美术的共性下寻找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情感倾向、审美理想融入到创作中去,努力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创作出了一批反映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优秀作品。
“新徽派美术”概念从产生到今天越来越被学界所认可,一系列成果的背后也凸显了新徽派美术的团队精神和旗帜作用,当前要乘势而上,继续挖掘新徽派美术的文化性和创造力,扩大新徽派美术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把新徽派美术做大做强。
注①《简议中国画派》周积寅:“从六朝起,作为文人学士的专业画家相继出现。专篇的中国画论不断问世,所谓“画乃吾自画”。于是绘画派系开始出现”。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1年
注②《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正版 俞剑华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注③《繁荣发展世纪之交的安徽美术事业》刘景龙 2000年
注④《汪世清书简》 鲍义来编 安徽省徽学学会 2008年
注⑤《艺苑查疑补证散考》 汪世清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注⑥《艺苑查疑补证散考》 汪世清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注⑦《黄宾虹画语》黄宾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注⑧《我的创作之路》赖少其 香港《文汇报》1988年7月2日
注⑨《关于赖少其近作的一种阐释》李伟铭 广州出版社1998年
注⑩《赖少其书画集》 天津人们美术出版社1993年
陈明哲简介:
陈明哲,安徽淮北市人,1972年6月生。先后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美术学院国画山水专业,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山水画方向研究生。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特聘教师,浙北中国画研究院仁量山水工作室助教,《文人画研究》杂志主编,徽社执行社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全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委员。出版《中国画名家年鉴·陈明哲卷》、《萧龙士和江淮画派之研究》、《新安探微》、《汪采白研究》等。
当代艺术家网
- 上一个:黄宾虹山水画的变与不变
- 下一个:张亚萌:书法界何来“好色”之风?